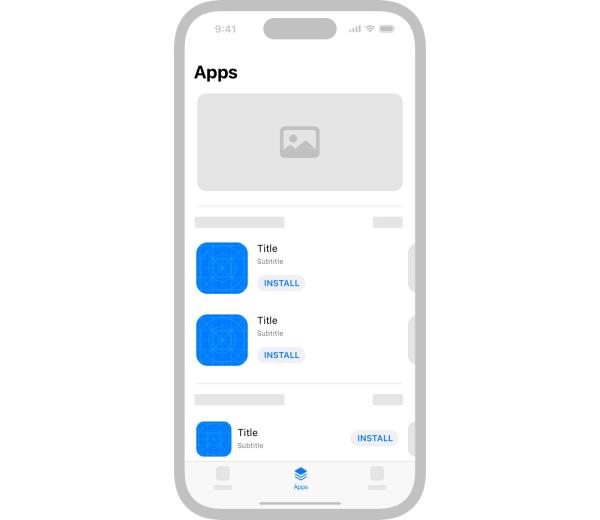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开始了三年的法医死亡调查员的职业生涯。受县验尸官的雇佣,我被派到死亡现场拍照、收集证据并进行采访。
新冠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环境,法医死亡调查员也不例外。然而,我们不是在家工作,而是被要求在处理前戴上外科口罩多达五次,而不是提供n95,并且在现场工作时使用最少的手套。是的,真的。不,这说不通。
虽然我们不是在拯救病人的生命,但我们以一种很多人没有的方式,与人体解剖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双手沾满了鲜血。我们把棉签塞进鼻子里,有一段时间还塞进直肠里,这样我们就能检测死者的病毒。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现场抽血和玻璃体,这样医生就不必这样做了(COVID-19在人死后很长很长时间内仍然可以检测到)。
尽管这个职业充满挑战,但它是值得的。我辞去了做了四年的儿童行为治疗师的工作,在家乡给验尸官做兼职,后来我转到一个大城市的验尸官办公室工作。我生活中的很多人都对我搬家的决定感到困惑,但有一个人一点也不惊讶:我的祖父。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祖父母一起过夜,他们会让我坐在电视机前,打开《48小时》(48 Hours),挑战我在最后发现凶手之前破案。我的祖父是一名退休的消防员和急救人员,他会递给我一本便笺簿和一支铅笔,告诉我:“列一张线索清单——它们告诉了你什么?”
我喜欢解决谜题——遇到一个谜并弄明白它的意义。作为一名死亡调查员,我要解开层层谜团。这个场景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死亡的情况?在我们通常看到的范围之外,人体还做什么?
在COVID-19期间了解我的职业的人对我的反应是“哇,你们一定很忙。”我不记得在疫情爆发多早的时候,我的反应从“COVID-19是自然原因,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转变为简单的“是的”。仅仅因为我们不需要调查与大流行相关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大流行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我们自己。
我们工作过度,人手不足,毫无准备。我们的停尸间里有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小床,因为尸体太多,而手推车不够用。人们生病了,由于政府削减预算,加班是不允许的,一些繁忙班次的调查人员从开始到结束都在现场。第二天,他们来到一堆要写的报告面前。这是因为大流行不仅仅是应对一种病毒——它是一场身体、情感和心理上的瘟疫。

2021年,我的城市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的谋杀率:在一个拥有90万人口的中西部大学城,发生了205起谋杀案。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小的数字,0.02%,直到你把它们放在冷却器里。这个数字只适用于城市范围内的死亡人数,整个县的死亡人数要多得多。
2021年,我县的自杀率也比前一年上升了10%。我们办公室专门为自杀死亡设立了一个新职位,也为过量死亡设立了一个类似的职位,2020年我们有859人,比2019年增加了48%。鉴于中西部地区多年来一直处于阿片类药物泛滥的状态,这一情况尤其令人担忧。
我们使用了一个在线数据库来追踪所谓的过量峰值。要被认为是高峰,我们需要在24小时内至少有6人死于服药过量。我们有时会在一周内多次出现这样的峰值,特别是在刺激支票减少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额外的钱花在药物上的结果)。
这些增长引发了我们办公室关于它们与大流行相吻合的理论。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一周中的几天和假期的模式,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呢?2020年,人们焦虑——2021年,他们绝望。人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医疗保险,无法去看心理医生,也无法乘车去美沙酮诊所。人们被困在充满压力的室内,与他们爱的人、他们容忍的人、他们虐待或被虐待的人在一起。似乎合乎逻辑的是,这些压力可能会导致他们做一些本来不会做的事情——那些把他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事情。
在此之前,我对工作的压力没有任何问题。人们喜欢对我说:“这项工作需要某种类型的人来做”,这是真的,但看到尸体只是对我们的一小部分要求。我们也会和家人交谈,尽可能地安慰他们,让他们把悲伤投射到我们身上。在他们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我们在他们家里是陌生人。他们要么爱我们,要么恨我们,但没有人愿意看到我们。
我一直都能泰然处之。我进入一个场景,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和这些家庭交谈,我是一名心理医生。我回到家,关掉电脑,不让自己去想那天我看到了什么。但在COVID期间,突然间,所有的创伤都开始从我大脑中精心标记的盒子里泄漏出来,我把它放在那里。我没有完全压紧的豆腐在我的煎锅里变成了脑浆。我跑步时排水沟里的塑料袋是一只人脚。我的工作无处不在。当世界停止运转,你的工作开始了,那份工作就变成了你的生活。
在2021年新年第一次换班后,我开始考虑离开这个领域。在轮班期间,我成为了最后一个在婴儿去检查前抱死婴儿的人,我抱着两个10岁以下的姐妹,我的值班伙伴帮忙把她们放在一个双线尸袋里,以防感染新冠病毒,我把她们父亲的尸体放在冷冻机的对面,因为在他对那些女孩做了那些事后,我无法接受他们坐在一起的想法。
在那一天工作10个小时的过程中,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超越典型愤怒的仇恨,怀疑邪恶是否真的存在,下班后我的脊椎底部一阵剧痛,不知何故既尖锐又沉闷。
我打卡下班,走到我的车旁,哽咽着直到我可以正常呼吸,开车回家。那是早上8点,冬天的空气很清爽,眼泪从我的睫毛上滴落下来。它们尝起来是苦涩的,那种眼泪来自于一份需要你去陌生人家里清理不是你造成的痛苦的工作。我是死亡调查员还是创伤监护员?我再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了。

我们办公室对我和同事所经历的压力的回应是在政府关门结束时:他们带来了一只治疗犬,让我们每隔几周就和它互动一次。我通常会坐在主管办公室的地板上哭泣,而不是去看狗。狗很好,但它们不能告诉你它们站在你站的地方,看到你所看到的。
我和我的医生谈过,医生给了我一个正式的创伤后压力诊断,我现在还在积极接受治疗。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资源,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我们办公室的经理们已经证明,尽管他们经常提醒我们提供反馈,但他们并不愿意接受反馈。我猜听到“做得更好”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反馈。
我开始申请类似的工作,其中大部分都需要应对紧急情况或确保正义得到伸张,直到有一天我认真地审视了我的生活。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已经开始渗透到我的骨头的疲惫感觉永远不会结束。所以,我听从我的身体。我的男朋友在佛罗里达找到了一份工作——阳光和凉鞋听起来像是中西部灰色天空和血淋淋的靴子的一个不错的改变。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朝着不同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噩梦还没有结束。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情况变得更糟了。当我不再强迫自己划分时间来度过每一天的时候,围墙倒塌了,创伤冲了进来。我从每个人都认为我是“特定类型的人”变成了一个听到汽车回火就会跳起来的人,如果质地让我想起太多尸体就吃不完一顿饭。
有些日子我很怀念它。我想念科学,想念解释发现,想念帮助辨认病人,想念结案,想念在办公室里和医生交谈,想听听他们对我所看到的奇怪而神秘的事情的看法。我真的很想念和我一起工作的团队,他们理解我对大多数人认为可怕的东西的迷恋。有几个调查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我之前离开了办公室,我听说后来也有几个人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推理是否和我的一样,但不管是什么,我都能理解。
我不能把这些感觉归咎于一种病毒,甚至是一场大流行,但我看到的趋势让我感到空虚。当人们否认COVID-19是真实的或危险的,或者当他们说它没有实际影响时,我经常想到这一点。我想尖叫——在我的脑海里,我真的想。我想告诉他们,我看过测试,看过证据,在长时间轮班后,我把证据从我的制服上洗掉,有时当我看到淋浴排水管周围的水变成粉红色时,我的皮肤上发现了证据。
我没有拯救生命,也许我永远也救不了即使我已经离开了这个领域,但我确实看到了生命被摧毁。我看到人们濒临死亡,人们试图拯救他们,人们试图给死者最后的尊严,但这些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我们被告知,事情正在恢复正常——无论正常是什么——但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正常永远不会再是一种选择。
布里奇特·戈尔登(Bridgette Golden)曾是一名死亡调查员,是土生土长的中西部人,有抱负的企业主,也是第一次写故事。她目前在佛罗里达州接受移植手术,并为一名公共辩护律师工作,希望能影响美国法律体系对心理健康的看法。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什么故事?找出我们在这里需要什么,然后给我们发一份建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