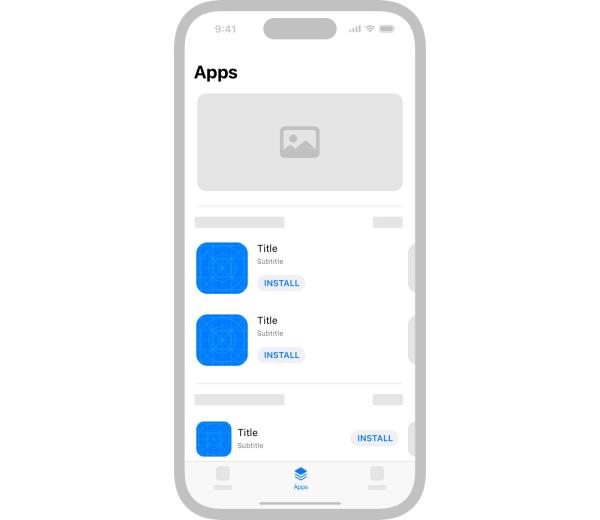这个故事最初出现在我们的欢迎你们的时事通讯中。在下面注册吧!
你好,你们。我的名字是鲍勃,我是一个大学橄榄球迷。
哇,等。超时!
Fanatic太好了。更确切地说,是疯子。
问问我的妻子就知道了,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南方女士,在比赛日,当我从体育场的座位上跳起来,扯着嗓子对下面的裁判大喊:“做你的工作!!”时,她经常觉得有必要向那些不幸处于火线上的陌生人道歉。
但我并不孤单。
即使你是刚到阿拉巴马州的人,你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发现,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与我有同样的痛苦,其中一些人的情况比我更糟。
我们性情温和,常去教堂做礼拜,用一盘自制的布朗尼蛋糕礼貌地欢迎隔壁的新邻居,本能地把车停在路边,帮助被困的司机修理漏气的轮胎。
但在秋天的周六,我们内心深处的足球海德先生就会出现,我们变成了精神错乱、令人恐怖的杜鹃鸟,不明智地把我们所有的自我价值投入到一场变幻莫测的比赛中,这场比赛是由容易犯错的年轻人玩的,他们容易在最不合适的时刻失误、绊倒或越位。
是的,我们是疯子。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嗯,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可能会选择一种更健康、压力更小的追求,比如观鸟或针线活。
不过,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大多数人生来就是这样的。
以我为例。我爱上了阿拉巴马州的橄榄球,因为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一个远房堂兄(约翰·卡尔顿·莫斯利)在1964年和1965年的科比教练的全国冠军球队中担任后卫,同时在66年的球队中担任后卫,如果那些扬基队的体育记者没有欺骗我们,把巴黎圣母院选为第一的话,那支球队应该是全国冠军。我的命运注定了,我一生都是巴马人。

但是,如果我早出生几十年,那时我的叔祖父(切斯特·克莱德·沃伦饰)是奥本大学的内线队员——在对阵佐治亚理工大学的比赛中,他在一个荣耀的时刻,用一个被封盖的脚踢回了一个触地得分——我可能会同样轻松地永远无畏,忠于橙色和蓝色。
不过,别搞错了,尽管我们阿拉巴马人热爱我们的大学橄榄球,但在内心深处,我们有点嫉妒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周六可以自由地长途开车去看芒通的树叶变色,他们不会把所有的情感投入到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上。
但我们记得,当图阿在“第二和26分”中将一角硬币扔到德文塔手中时,那种兴奋的感觉,以及,对我的奥本朋友来说,看到克里斯·戴维斯在“六分”中快速跑到边线上的那种纯粹的喜悦。
在这样的时刻,当所有压抑的焦虑爆发为肆无忌惮的喜悦时,我们被提醒,这就是我们最初成为粉丝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释怀。
不管我们喊“滚吧,潮水!”或大喊“战鹰!”,不过,双方都同意这一点:
我们正处在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大学橄榄球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