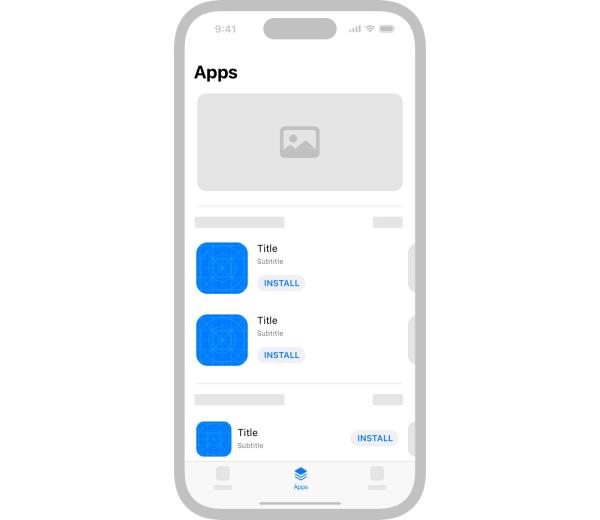纽约(美联社)——在不可预见的未来,莱拉·哈达德(Laila El-Haddad)有一个任务:让她的巴勒斯坦同胞的声音,连同他们寻求帮助的请求,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本周,在她位于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的家中,哈达德疯狂地接听记者打来的电话,这些记者寻求她在加沙问题上的专业知识,而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则试图引起当地民选官员的注意。
在通话间隙,这位45岁的母亲兼作家查看了全球即时通讯应用WhatsApp,查看她在加沙的家人在短暂的电力和互联网接入窗口期间的最新情况。此后,以色列切断了电力供应,互联网中断使许多人难以保持联系。
埃尔-哈达德说:“我只是想通过尽我所能来保持理智。”
对于许多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来说,当他们挣扎着听到加沙亲人的消息时,他们感到无助和绝望。在燃料和水短缺,没有电,现在北部被迫撤离的情况下,管理和向加沙平民提供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色列连日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并威胁要发动地面进攻,以回应哈马斯上周末对以色列的袭击,那次袭击造成1300人死亡。加沙卫生部星期六说,过去几天来,被围困地区有2200多人被杀,其中包括724名儿童和458名妇女。随着人道主义危机的逼近,这个数字预计还会上升。
但即使在本周之前,对于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来说,前往加沙探亲是一段漫长、疲惫和艰难的经历,大多数住在加沙的人永远无法离开。与以色列裔美国人不同,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说,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在危机时刻自由地帮助他们的亲人。
Mohammad AbuLughod住在密尔沃基郊区,他在加沙的家人通过太阳能电池板给手机充电,他从手机上接收零碎的更新信息。他的家人与美联社分享了这些信息:
家里的一位长者死于空袭。在决定留在家中之前,他们试图在一所联合国学校寻求庇护。学校被空袭破坏。儿童死亡。建筑物已沦为瓦砾。他们不知道邻居们是否还活着。现在他们三代人都住在一所房子里。当炸弹来临时,他们会一起死去。没有人会独自生活。
“我觉得我生活在一场噩梦中,”一位亲戚在给家人的信息中写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没有办法提供支持,我们不能给他们钱,钱可能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买的,”他说。
迪安娜·奥斯曼在加沙的年轻侄子在Instagram上给她发信息,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能和她说话了。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住在芝加哥郊区的奥斯曼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你怎么能说些什么来安慰一个面临死亡的人呢?”
居住在新泽西州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哈宁·奥卡尔(Haneen Okal)目前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被困在加沙地带。她在怀孕期间去了加沙,9年后回家探亲,并计划回到新泽西生孩子。但在经历了医疗紧急情况后,她于8月在加沙生下了孩子,此后一直留在那里。
本周早些时候,就在她准备通过拉法与埃及的过境点离开加沙的几分钟前,以色列的空袭使过境点无法使用。她和她的孩子们星期六回到了拉法过境点,希望美国政府能允许他们安全撤离。她说,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官员还没有告诉她,他们是否会帮助她离开。奥卡尔的丈夫阿卜杜拉(Abdulla)恳求新泽西州的美国政府把他的家人接回家。
“加沙地带没有安全的地方,”哈宁·奥卡尔(Haneen Okal)在通过WhatsApp发送给美联社的一段录制视频中说。“我的孩子们感到很害怕. ...请帮助我们安全撤离。”
本周,许多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痛苦地看着海外的以色列人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后纷纷前往以色列,报名参加军事预备役或在地面提供援助。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表示,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选择。
加沙地带只有25英里(40公里)长,人口230万,基本上是一片黑暗,以色列的封锁使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变得更加困难,那些在加沙有家人的人只能在远处观望,当他们的家人努力寻找安全时,他们感到无能为力。
“对我来说,现在看到美国公民甚至在此之前就享有特权,可以进入我的国家,而我的丈夫,一个巴勒斯坦人,他的父母和祖父母被迫逃离家园,却享受不到这种待遇,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马里兰州的作者埃尔-哈达德说。
今年夏天,奥斯曼和她的家人从芝加哥郊区前往加沙,她说这个过程在精神上、身体上和官僚上都很困难。奥斯曼的大家庭住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但她丈夫的家人在加沙。如果她想去看望她在西岸的家人,她必须独自去,她的丈夫和大多数持有加沙身份证的人一样,不能去以色列占领下的西岸。
“当我在加沙的时候,我在西岸的家离我只有40英里(64公里),”奥斯曼说。“但要找到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行不通的。”
几年前,在较为和平的时期,Nahed Elrayes和他的父亲花了几天时间试图从特拉维夫进入加沙,去看他身患绝症的祖母的最后时刻。
“以色列人就是不让我们进入加沙,”他说。在尝试的第三天,Elrayes的祖母去世了,以色列军队终于允许他们进入参加葬礼。
“我永远不会忘记和父亲在一起的那一天,”埃尔瑞斯说。“对我们的人性没有尊重。”
如此多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故事充满了渴望、失落和他们的历史正在被抹去的感觉。许多巴勒斯坦家庭都是最近才成为难民的。加沙今天人口如此密集,部分原因是1948年围绕以色列建国的战争期间,大批巴勒斯坦人逃离了现在的以色列。
这是1948年纳克巴的回响,或“灾难”,困扰着阿布卢格德和他的家人——最初来自巴勒斯坦城镇雅法的难民,现在是以色列的雅法——当他们本周看到大规模撤离加沙的场景时。令人担忧的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就像1948年被迫离开家园的那些人一样,将永远无法返回家园。对于许多失去土地和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来说,身份是他们所剩下的一切。
穆罕默德的女儿Amirah AbuLughod说:“目前最沉重的是,世界将看到一群人被无情地杀害,并被实时驱逐,并相信这是正确的,OK的,公正的。”
为了应对这一可怕的前景,哈尼·阿尔马德洪说,他和他在美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同事们正在全力支持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尽管面临挑战,仍努力向加沙地区的人们提供援助。本周,11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加沙的空袭中丧生。
“现在加沙没有英雄。每个人的损坏。每个人都在埋葬某人,”阿尔马德洪说。我希望我是错的,但这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更多的人会失去生命,但没有人会被追究责任。”
____
诺琳·纳西尔(Noreen Nasir)是美联社种族和民族小组驻纽约的成员。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她:twitter.com/noreensnas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