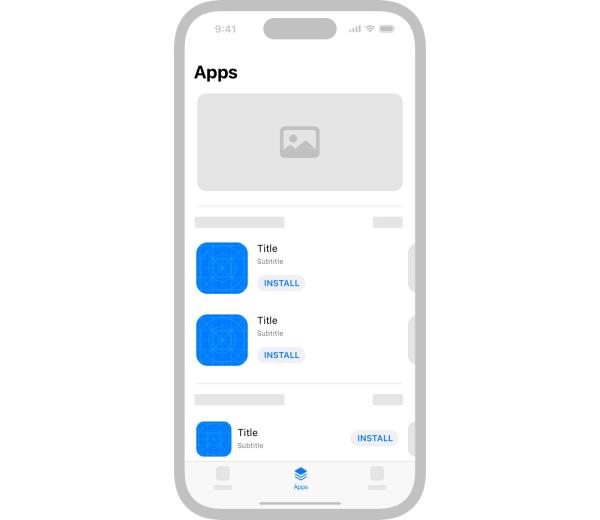即将加入下一届以色列政府的宗教党派希望通过《回归法》(Law of Return)限制移民以色列和获得以色列国籍的人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建议剔除目前有资格的两个关键群体:犹太人的孙辈和非东正教皈依者。
有迹象表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有他们的支持,这位被任命的总理本周将负责前苏联集团国家aliyah的机构Nativ的控制权移交给了一个极右翼宗教党派的领袖,该党派历来敌视非正统派运动,并蔑视那些他认为不是真正犹太人的人。
根据与内塔尼亚胡达成的联合政府协议,反lgbtq的极端党派Noam党的领导人阿维·毛兹(Avi Maoz)也将被任命为总理办公室的副部长,负责促进“犹太民族认同”。
俄罗斯和乌克兰多年来一直是以色列阿利亚的主要来源。自从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这次入侵导致两国数以万计的战争难民来到以色列海岸。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犹太教徒——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犹太母亲的孩子——而是犹太人的子孙。由于毛兹控制了纳提夫,今天有资格获得阿利亚的大部分人可能会失去这个权利。
由于《归国法》中的“孙辈条款”,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的以色列人已经在以色列扎根。如果宗教党派一意孤行,数百万人将失去这一权利。
但是,他们不会是对回归法的拟议修订的唯一受害者。如果被拉比从“错误的”(非正统的)运动中转变过来,那些有选择的犹太人也会吃亏。
谁会被认为对以色列来说不够犹太?以下是他们的一些故事……
叶莲娜多布林
叶莲娜多布林。
出生于乌克兰的移民律师多宾被认为有资格获得aliyah,因为她的祖父是犹太人。她在18岁时独自来到以色列,这是一个为前苏联高中毕业生设立的特殊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为父母和兄弟姐妹带路。
几年后,多宾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加入了她的家庭。那时,多宾已经以战斗士兵的身份服完兵役。
现年38岁的多宾在服兵役期间,曾被鼓励参加由军队开办的一个特殊的东正教皈依项目。她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但很快就退出了。她说她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我可能不是一个哈拉克犹太人,但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犹太人,没有人能告诉我不是这样,”她说。“在乌克兰上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会叫我‘肮脏的犹太人’。’但在以色列,我被告知我不够犹太人。”
多宾住在特拉维夫以东的城市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由于乌克兰战争,他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忙于工作。她说,她的许多客户都是第三代犹太人——正是即将上任的政府希望把他们赶出美国的那类人。
“这太不公平了,尤其是考虑到那里现在发生的事情,”她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政府应该扩大第四代人的资格。”
多宾的许多客户在完成所有移民手续之前就被允许进入以色列。“现在,他们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可能最终会失去他们对阿利亚的权利,”她转述道。
卡罗丽娜Gunia
卡罗丽娜Gunia
Gunia出生在立陶宛,五年前与在那里学习的一名以色列犹太人结婚后移居以色列。她在六个月前通过以色列的改革运动完成了皈依犹太教的过程,目前正等待通过回归法获得公民身份。
“对我来说,被承认为犹太人和以色列公民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我被接受了,”这位31岁的建筑师说,他能说流利的希伯来语和英语。“但现在我真的很紧张,因为大家都在谈论修改《回归法》。”
虽然她不是生来犹太人,但古妮亚说,甚至在遇到她未来的丈夫之前,她就一直觉得自己与以色列和犹太人有一种联系。“我在以色列有好几个亲戚,因为我叔叔娶了一个犹太女人,并成为了阿利亚。所以在认识我丈夫之前,我就去过以色列,认识那里的人。”
在以色列呆了几年之后,她说:“我真的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比我在立陶宛的感觉要强烈得多。”
古妮亚和她的丈夫住在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改革运动旗舰教会拜特丹尼尔的活跃成员。她说,想到她的改革计划可能不被国家承认,“我非常难过”。
“虽然我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我热爱犹太传统,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意愿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她补充道。
利亚琼斯
利亚琼斯
琼斯是芝加哥伊曼纽尔教堂(Congregation Emanuel)的前任主席,她很自豪地带领这座改革派犹太教堂度过了其145年历史上最动荡的两年:在她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新冠疫情,仪式都在Zoom上举行。
琼斯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世俗基督教家庭出生和长大,她说她的犹太教之旅很不典型。这位45岁的营销主管说:“当时我迷上了一个犹太人,所以我读了《理解犹太教的傻瓜指南》,在里面我找到了一种真正适合我的宗教。”“这是我第一次能够从自己的一堆信仰中理清头绪。”
在皈依约五年后,琼斯开始认真考虑aliyah的问题。“最终,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我感觉我会让我的妹妹承担所有的工作,帮助我们年迈的父母,”她说。
她定期访问以色列,大约一年一次,尽管她承认自己在这个犹太国家从未感到完全舒适或受欢迎。她说:“我一直知道我在以色列的地位取决于政府的任性,我在那里从来没有真正感到安全。”“我知道,如果我结婚生子,我的婚姻在那里不会被接受,我的孩子也不会被承认是犹太人——这对我来说真的很伤心。”
如果根据宗教党派的要求修改《回归法》,琼斯将失去做阿利亚的权利。一想到这些,她就开始考虑是否要继续去以色列旅行。“为什么我要去我认为是我的宗教家园的地方,而执政的政府不把我看作是人民中的一员?”她问道。
与此同时,她担心,如果反犹主义继续在美国蔓延,她将无处可逃。“我唯一的公民身份是美国,”她说。“取消我的回国权意味着,如果美国的情况变得更糟,我就无处可去了,这真的很麻烦。”
亚历山大Koff
亚历山大Koff
他的祖父出生于一个犹太母亲,1992年,他是家族中第一个获得阿利亚的成员。来自乌克兰的考夫,三年后和他的直系亲属一起来到这里。如果当时没有“孙子条款”,他和他的兄弟将被剥夺移民以色列的权利。
“讽刺的是,在前苏联,我们被认为是犹太人,因为宗教是由那里的父亲决定的。在这里,我们被告知我们不够犹太——尽管我们在军队服役,但我们对经济有贡献,是社会的有生产力的成员。”
在讽刺那些想把他这样的人赶出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时,科夫补充道:“我们不会整天坐在那里祈祷。
49岁的科夫住在南部港口城市阿什杜德,从乌克兰进口农业机械。他有两个女儿在部队服役。上周,他自豪地注意到,三个女儿同时为国效力。他说:“在过去的10年里,尽管我不再被要求服预备役,但我每年都去做志愿者。”“所以上周我也在部队里。”
当被问及他对限制回归法资格的提议有何看法时,考夫回答说:“这太荒谬了。这个国家有一半我认识的人,就像我一样,都是因为‘孙子条款’才来到这里的。”
海蒂施耐德
海蒂施耐德
作为一个年轻的人,施耐德在罗马天主教家庭长大,是一个精神探索者。在接触了佛教和新教之后,她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一个犹太人,并开始研究犹太教。她说:“我觉得自己就像金发姑娘,因为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东西。”
65岁的施耐德30多年前通过保守主义运动皈依犹太教,从那以后就一直活跃在她的家乡明尼阿波利斯的犹太生活中。她不仅担任过教会的主席,还在当地的《塔木德律法》中教授有关以色列的课程。她现在担任马索提基金会的主席,这是马索提世界运动的筹款机构,隶属于保守犹太教。
施耐德成年后一直是一个骄傲而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她说,以色列政府考虑把她和她的孩子赶出以色列的想法“非常伤人”。
“我希望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她说,“因为我很难相信这是大多数以色列人想要的。所以,虽然我受到伤害和悲伤,但我不会放弃——我绝不是认输。我仍然爱以色列,仍然爱以色列人。”
施耐德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她说,即使以色列决定不接受她作为犹太人的身份,她也不会对皈依犹太教的决定有任何犹豫。“犹太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如此多的意义、如此多的爱和如此多的社群,”她说。“我怎么会后悔呢?”
丹尼尔Farcas
丹尼尔Farcas
在移民以色列之前,59岁的法卡斯曾是智利的一名议员,代表中间偏左的民主党。他在18个月前离开以色列,在加布里埃尔·博里奇当选总统之前。博里奇曾是一名学生领袖,对以色列怀有敌意。
法卡斯是一个哈拉卡犹太人,所以他和他的孩子不会受到《归国法》拟议修改的影响。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以色列向散居在外的犹太人传递的信息深感担忧,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智利这样的国家的犹太人,在那里,他们只是生活在日益反以色列的环境中的一小部分人。
他说:“当你花这么多时间试图保卫以色列时,你至少需要得到你正在保卫的人民的支持。”“但相反,我们却在背后被捅了一刀。”
法卡斯指出,智利1.8万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属于非正统派运动,而即将上任的以色列政府中的许多人认为这些运动是不合法的犹太教形式。
“以色列人不明白在偏远地区的犹太人是多么孤独,尤其是当反犹主义再次抬头的时候,”Farcas说,他住在内坦亚,为一个帮助在以色列的智利犹太人的组织工作。
?玛利亚斯莱文
?玛利亚斯莱文
因为她的祖父是犹太人,40岁的Slavin有资格获得aliyah。1999年,她离开乌克兰前往以色列,最终嫁给了一个俄罗斯移民,她讽刺地称他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但她从未考虑过正式皈依犹太教。她解释说:“我对宗教胁迫非常反感。”
斯拉文在一家印刷厂的质量控制部门工作,和许多非哈拉卡犹太人的前苏联移民一样,她说自己在以色列从来没有完全被接纳过。
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说:“过几年你就会开始明白,这里没有人真正关心你,你完全要靠自己。”她和家人住在特拉维夫市外的霍伦。她说,在她结婚之前——在塞浦路斯的一个仪式上,因为她不被拉比机构承认为犹太人——她甚至考虑过离开这个国家。
当被要求评论《归国法》的修改提议时,Slavin说:“这太愚蠢了。对纳粹来说,我们是犹太人,应该被扔进毒气室。对以色列来说,我们不够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