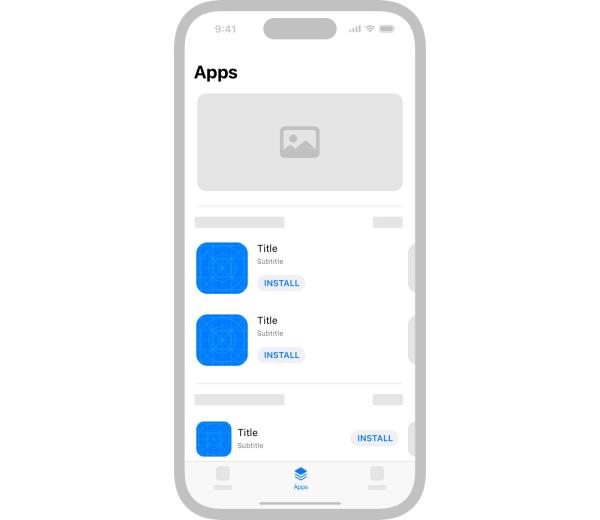1830年,英国艺术家奥古斯都·厄尔在悉尼画的一群罪犯。
在被运送到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囚犯中,有一小群人被指控犯下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罪行。
从1788年到1868年,大约有16.2万名囚犯被送到那里,其中至少有3600名政治犯,包括工会会员、民主倡导者和爱尔兰革命者。
当他们到达时,这些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政治,而是和其他许多人一起联合起来,对殖民地进行政治抵抗。
历史学家哈米什·麦克斯韦-斯图尔特和托尼·摩尔博士表示,这是被遗忘的囚犯故事的一部分,他们正在塔斯马尼亚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举办一个名为“解开镣铐”的巡回和在线展览。
作为一项为期四年的项目的一部分,他们的团队使用了来自澳大利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名单的罪犯档案的大量数字化信息,分析了几十年来交通运输及其他方面的趋势。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抵制的规模,”新英格兰大学的遗产和数字历史专家麦克斯韦-斯图尔特在接受ABC RN的《深夜现场》采访时表示。
在流放罪犯的时代,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中期。这见证了技术和发展的巨大飞跃,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
抵制来自卢德分子(Luddites)和摇摆暴徒(Swing Rioters)等团体,他们抗议工资和工作条件。其中一些人与当局发生冲突,被送往现在的澳大利亚。
例如,乔治·洛夫莱斯(George Loveless)是卫理公会的世俗传教士和劳动者。他在多塞特郡的托尔普德尔(Tolpuddle)村领导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工会,名为“农业工人友好协会”(Friendly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workers),抗议工人工资的降低。
“英格兰北部也有工会。这是允许的。但不是在南方,而是在这些大地产上,”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传播与媒体研究系主任摩尔(Moore)解释说。
1834年,这六名男子因秘密宣誓而被定罪,并被送往悉尼和霍巴特,成为著名的“Tolpuddle Martyrs”。经过国内的抗议,他们于1836年被赦免并返回。
 nan Picture Library / Photo12 via AFP)">
nan Picture Library / Photo12 via AFP)">
1834年在伦敦举行的抗议驱逐托尔普德尔殉道者的示威游行。
还有一些罪犯被摩尔称为“革命者和反叛者”。其中包括2000多名爱尔兰激进分子,他们来自联合爱尔兰人和青年爱尔兰等组织。
摩尔说,总的来说,这些政治犯是“丰富多彩的运动名人录”。
他特别提到了丽贝卡的女儿们,这是一群“变装的通行费和收费公路破坏者”,他们对威尔士道路的私有化和收费感到愤怒。
虽然目前的研究显示,被送往澳大利亚的政治犯总数约为3600人,但摩尔表示,实际人数可能超过4000人。
他说,一些罪犯被归类为“骚乱者、破坏和平者或非政治性行为,比如盗窃”。但是当他们查看记录时,他们发现他们在罢工。
“就这样数下去。”
托马斯·缪尔是摩尔最喜欢的政治犯之一。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是一名苏格兰律师和工人权利活动家,他被驱逐到澳大利亚,但设法乘坐一艘毛皮贸易船逃脱。

缪尔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苏格兰律师,他主张对政治制度进行民主改革,领导了人民之友协会。
摩尔说:“他敢于在18世纪90年代的苏格兰与工人交谈并组织工人,他敢于成为一名媒体活动家。”
“(他)在写作,写小册子……分发禁书,比如托马斯·潘恩的《人权》。”
作为法国大革命后英国政府镇压的一部分,他被判犯有煽动叛乱罪并被流放。
但缪尔后来设法乘坐一艘美国毛皮贸易船逃离了新南威尔士州。
他横渡太平洋,从温哥华岛到墨西哥城再到古巴,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幸,其中包括他的一艘船被击中而失去了一只眼睛。
“这个现在残废(但仍然)英俊的年轻人来到了法国。他被宣布为共和国公民,并在流亡中加入了苏格兰的名录,”摩尔说。
许多犯人在服刑期间在澳大利亚殖民地从事政治活动。
但麦克斯韦-斯图尔特和摩尔说,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点,需要对更广泛的罪犯项目进行重新思考。
摩尔说:“事实上,罪犯是一群被利用和剥削的不自由的劳动力……为了建立殖民地,为了建设经济,为了让这些殖民地的雇主致富。”
“在澳大利亚,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交通运输是建造殖民地的巨大机器。”
换句话说,成千上万的罪犯在可怕的条件下被剥削,夺取原住民的土地,并将其开发为农业和其他项目。
麦克斯韦-斯图尔特还指出,“交通工具的一个妙招是大大增加了句子量”。
“如果你在英国或爱尔兰被判入狱,很可能是按月计算的,(因为)把一个人送进监狱是非常昂贵的……但如果你被判流放,最低刑期是7年。”
“这就像铸造了200万年的不自由劳动力,供英国人使用。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是……从(大多数)小偷那里偷时间去偷一个大陆。”
于是,囚犯们起来反抗这种残酷而漫长的生活。
麦克斯韦-斯图尔特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确实没有自下而上的团结。”
“但通过数字化拼凑大量法庭记录和大量罪犯的惩罚记录,我们现在知道,在新南威尔士州和范迪门斯地(现在的塔斯马尼亚州),至少有1.1万起集体行动,其中包括罪犯一起抗议。”
1804年的城堡山战役就是其中之一。
康沃利斯侯爵在18世纪90年代将数百名爱尔兰囚犯带到新南威尔士州。
1798年爱尔兰叛乱失败后,数百名爱尔兰囚犯被运往新南威尔士州。
1804年,这个组织中的许多人计划攻击殖民政府所在地,征用一艘船,然后返回爱尔兰继续在那里战斗。
“‘死亡还是自由’的呼声响起,”摩尔说。
但是城堡山的叛乱没有成功,其领导人和参与者未经审判就被绞死,而其他人则面临着被流放到煤河(纽卡斯尔)镣铐监狱等惩罚。
被送往澳大利亚的女犯人的生活条件尤其恶劣。
麦克斯韦-斯图尔特说:“我们能够证明,一名女罪犯被单独监禁的每一天,预期寿命都会减少10天。”
“(而且)他们的性取向受到监管。”
麦克斯韦-斯图尔特说:“她们逃跑的比率高于男性囚犯,这是英国唯一一个不自由的劳工殖民地。”
“他们还积极反对被迫在周日工作,而周日是罪犯的法定休息日。”
以Fanny Jarvis为例,她的故事是由研究人员Monika Schwarz博士在项目中发现的。
范妮是斯塔福德郡的一个仆人,她16岁时偷了主人的衣服,并于1836年被送到了范迪门之地。
她是“快闪族”团伙的一员,参与了卡斯卡迪斯女性工厂的一次重大骚乱,在那里女性控制了工厂。
麦克斯韦-斯图尔特说:“有一个抗议网络,这个年轻的青少年罪犯就在他们的中心。”
这不仅仅是罢工和其他工作场所的行动。
摩尔说:“还有政治罪犯的媒体激进主义——他们在这里当囚犯的时候编辑报纸。”

在被驱逐到现在的塔斯马尼亚之后,威廉·卡夫伊成为了一名工会领袖,并为工人的权利而战。
他还提到威廉·卡夫伊(William Cuffay)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
卡菲是宪章运动领袖、工会成员,也是奴隶的后裔。他被认为是一个有天赋的演说家,经常把他的信息传达给大众。
但在1848年,卡菲被指控“密谋发动战争”反对维多利亚女王,并被判处21年监禁。
他后来被赦免,但没有选择返回英国,而是留下来为工人权利和民主改革而竞选。
“他成了塔斯马尼亚的鲍勃·霍克。他成为一名工会领袖,反对严厉的《主人与仆人法案》,这是一种吉姆·克劳式的试图在废除罪犯主义后保留它的做法。”
麦克斯韦-斯图尔特和摩尔都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挑战一些对罪犯的刻板印象。
摩尔说:“罪犯要么被视为情景喜剧,就像‘那些流氓不是足够幸运地来到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吗?’要么被视为马库斯·克拉克(Marcus Clarke)版本的地狱古拉格集中营……他们缺乏能动性。”
“当我们说不的时候,他们集体反抗,而且反抗的规模很大。”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能够塑造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的开端”。
19世纪中后期,围绕工人权利、平等主义和民主的激进甚至叛国思想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生根发芽,并继续定义着今天的澳大利亚。
这篇报道最初由美国广播公司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