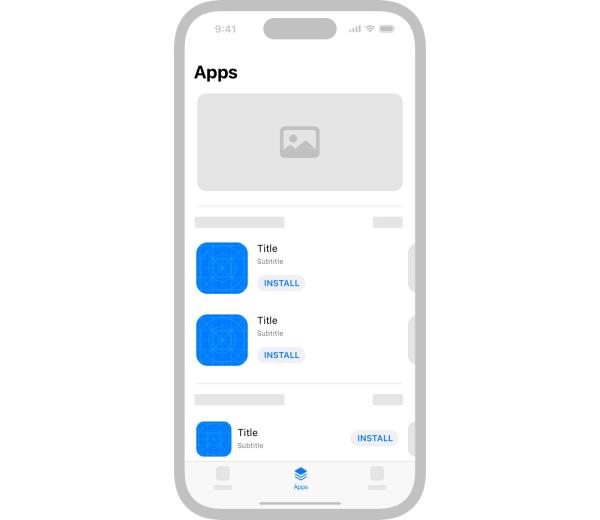斯蒂芬·麦克德莫特
斯蒂芬·麦克德莫特
周日晚上,来自爱尔兰极右翼运动的人士聚集在都柏林,为两名新当选的地方政府官员干杯。
加文·佩珀(Gavin Pepper)和马拉奇·斯蒂森(Malachy Steenson)都在首都不同的反移民抗议活动中具有影响力,他们将在未来几周内在都柏林市议会(Dublin City Council)获得席位。在此之前,爱尔兰围绕移民问题持续了18个月的争论在上周末达到了高潮。
选举成功几小时后,这对夫妇坐在Erin Go Bragh旗帜和一桌啤酒后面,在爱尔兰自由党领导人赫尔曼·凯利(Hermann Kelly)的旁边拍照,后者随后在X上分享了这张照片。
“有时候只是庆祝一下,笑一笑就好了,”凯利在照片的配文中写道。
然而,对凯利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他兄弟般的表演,以及在佩珀和斯廷森的胜利中沐浴在聚光灯下的企图,掩盖了三人在选举中截然不同的命运。
作为当地独立人士参选的Steenson和Pepper成功地利用了社区内对移民的担忧,很明显,周六晚上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人都有可能赢得都柏林市议会的席位。
爱尔兰自由党在20个地方政府中只选出了一名议员;该党有29名候选人未能赢得一个席位,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参加竞选。
这表明了极右翼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的更广泛的故事,在地方选举中,对移民的关注被独立人士成功地吸收了。
但是,尽管这次只赢得了949个地方政府席位中的5个,但爱尔兰的运动已经出现了萌芽。
极右翼观点已经在爱尔兰的政治话语中站稳了脚跟,如果不同的派别能够合作,有证据表明,它们在未来会蓬勃发展。
近年来已经有极右翼势力增长的迹象,特别是考虑到今年参加选举的候选人数量。
据《华尔街日报》统计,有100多人在地方选举中以极右翼政纲参选,几乎是参加2020年大选人数的三倍。
他们包括五个注册极右翼政党的候选人——凯利的爱尔兰自由党、民族党、农民联盟、爱尔兰第一和爱尔兰人民——以及少数独立人士,其中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强大的追随者。
在150多名候选人中,有5名候选人最终当选:都柏林市议会的Steenson和Pepper;参选南都柏林郡议会的爱尔兰自由党成员格伦·摩尔;国家党的帕特里克·昆兰,他站在芬加尔;以及基尔代尔的无党派人士汤姆·麦克唐纳。
周日,赫尔曼·凯利与斯蒂森(右二)和佩珀(右四)一起庆祝
尽管他们与其他发表反移民观点的候选人(尤其是一些农村独立人士)占据了类似的空间,但极右翼候选人因其更为极端的政治品牌而与众不同。
极右翼人士并不是简单地质疑政府的移民政策,而是使用了无耻的种族主义观点,充斥着阴谋论思维和错误信息。
这源于种族民族主义的基础——一种认为国籍是由一个人的种族定义的信念——它认为爱尔兰的社会结构正因移民和非白人的存在而退化。
独立候选人弗格斯?鲍尔(Fergus Power)就是基于这种极端观点在社交媒体上积累了大量追随者的人之一。去年,他在Dáil上被点名为散布谣言“煽动”都柏林骚乱的人之一。
去年,他在Dun Laoghaire(他作为当地候选人参加竞选)发布了一张照片,并配上文字:“大声说出来,清楚说出来:让那些肮脏的无证经济移民、可能的杀人犯和潜在的强奸犯……离开这里”。
爱尔兰第一党的领导人德里克·布莱格曾是弗莫当地的候选人,同时也是爱尔兰南部一个欧洲席位的候选人。他在本月早些时候鼓励人们投票,声称“外国强奸犯通过在爱尔兰申请庇护来避免被驱逐出境”。
民族党在其网站上表示,该党支持“结束所有大规模移民进入爱尔兰”,而爱尔兰人民同样声称,现任政府正在“摧毁爱尔兰”,其政策包括“开放边界”和“全球主义议程”。
与许多抗议收容难民的人不同,极右翼候选人和政党在竞选中也对女性、LGBT问题和伊斯兰教持极端保守的观点,他们同样把这些作为爱尔兰持续衰落的证据。
在新桥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赢得基尔代尔郡议会席位的汤姆·麦克唐奈(Tom McDonnell)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爱尔兰的出生率,他说:“如果没有女性生育,我们这个物种就会灭绝。”
“爱尔兰优先”的另一位候选人菲利普·德怀尔(Philip Dwyer)在社交媒体上宣扬阴谋论,他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采访中声称,来自中东的穆斯林是暴力犯罪的幕后主使,这些暴力犯罪在他们抵达爱尔兰之前显然从未在爱尔兰发生过。
这种说法在试图利用当地对庇护住宿的不安并将其转化为选票的政客和经常分享阴谋论或表达边缘政治观点的极右翼人物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
汤姆·麦克唐奈周三在新桥当选
参加竞选的极右翼候选人的绝对数量表明,该运动内部有信心,认为公众对其信息持开放态度,或者认为其个性足以填补爱尔兰政治中保守民粹主义的空白。
正如凯利的“庆祝”所证明的那样,五名极右翼议员的当选只会增强这种信心,并增强运动内部的自信,即它正在取得成功。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它将从大城市开始,蔓延到所有地方,”爱尔兰第一党的领导人德里克·布莱格(Derek Blighe)在佩珀和斯蒂森在都柏林当选后表示。
他们的势头可能会因为输给更温和的独立人士而有所减弱,后者能够通过在移民或反绿色问题等类似问题上的运作来获利,而不会在方法上过于极端。
但很明显,上周末的选举结果标志着爱尔兰极右翼的分水岭。
除了极右翼候选人的实际成功之外,与前几年相比,极右翼候选人的支持率普遍上升。
在上次大选中,表现最好的极右翼候选人只获得了2%的第一选择选票,没有人当选;这一次,超过70人获得了至少2%的选票,即使是在他们没有投票的地区。
尽管各党候选人的总体表现不佳,但这70名候选人中的大多数都代表了五个注册的极右翼政党之一。
这可能部分是由于被选为政党候选人的类型,以及他们的政策。
摩尔和昆兰的成功标志着爱尔兰自由党或民族党自10年前成立以来首次有候选人当选。
摩尔是一名年轻的活动人士,他说他去年才加入该党,他声称自己是在目睹了都柏林的暴力犯罪后参与政治的。
为了传递信息,他在讨论爱尔兰移民问题时顺便提到了“大更替”(一种声称西方白人正在被移民取代的阴谋论)。
但他代表了爱尔兰自由党近年来更广泛的旅程;它的候选人不再是一群著名的阴谋理论家和反欧盟的乌合之众,如本·吉尔罗伊和多洛雷斯·卡希尔,而是一群观点不太为人所知的年轻无名者。
爱尔兰自由党的格伦·摩尔X.com / @moorsey100
昆兰在国家党中也是类似的人物。
该党在2020年大选中最突出的两位候选人,有争议的领导人贾斯汀·巴雷特和菲利普·德怀尔,在被赶出(德怀尔的情况)或在持续的领导权争议中被边缘化(巴雷特的情况)后,这次没有参加当地的党内竞选。
这一次,它的12名地方候选人都是没有社交媒体恶名包袱的新面孔,他们既展望过去,也展望未来。
“我们是不可避免的,民族主义是爱尔兰的未来——这是正确的,”他在周日赢得选举后表示。
“这是大卫对歌利亚的局面,大卫正在装弹弓,准备推翻这个政权。”
国家党候选人帕特里克·昆兰的照片
但是,如果从极右翼政党的广泛选举结果来看,他们可能颠覆爱尔兰政治体制的说法几乎是不可信的。
尽管摩尔和昆兰各自取得了成功,但作为极右翼候选人,他们是明显的异类,他们似乎是尽管是政党政治家而不是因为政党而当选的。
在被拍到与斯廷森和佩珀庆祝的第二天,凯利在卡斯尔巴的米德兰兹西北欧洲伯爵告诉记者,爱尔兰选民普遍倾向于“经济自由、社会保守和民族主义”。
但是,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存在明显空间的政治环境中,五个极右翼政党几乎没有产生影响,这是对他们事业的一种谴责。
爱尔兰自由党(Irish Freedom Party)和国家党(National Party)在首轮投票中可能已经突破了2%的门槛,但爱尔兰自由党(Irish Freedom Party)的30名候选人中只有4人获得了5%以上的选票,而国家党(National Party)的12名候选人中只有2人获得了5%以上的选票。
爱尔兰自由党领袖赫尔曼·凯利(左)在当选后将加文·佩珀高高举起
正如在选举中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取而代之的是少数独立人士,他们更有优势,无论是通过像Pepper这样的品牌认知度,还是像Steenson和Kildare的Tom McDonnell这样的当地熟悉的角色。
社交媒体的存在以及一些独立人士参与反移民抗议或反对寻求庇护者住宿的地方运动,最终帮助他们在选举中取得了强劲的表现。
佩珀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活跃在芬格拉斯地区的反移民煽动者,近年来在极右翼社交媒体上声名显赫。
他经常在X上发布有关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视频,并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反移民抗议活动中露面。
Steenson是一名在东墙很有名的当地律师,在2022年底爱尔兰第一次大规模反对庇护住宿的抗议活动中,他也担任了反移民抗议者的发言人。
马拉奇·斯蒂森在周日的滚动新闻节目中当选后接受媒体采访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成功当选的无党派人士。
在克里,米歇尔·基恩(Michelle Keane)获得了10.2%的第一选择选票,但在卡斯尔岛(Castleisland)以微弱优势错过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席位。
她以前曾在她的社区里反对安装桅杆,最近又参与了反对在特拉利安置寻求庇护者的抗议活动。
凯文·科伊尔(Kevin Coyle)曾在阿尔坦-白厅任职,并在库洛克(Coolock)的反移民抗议活动中声名显赫,他也有望在都柏林市议会(Dublin City Council)获得席位,但周日下午由于缺乏调动,他的机会落空了。
他们更多的是草根风格的竞选活动,没有作为政党候选人所产生的距离感,这给他们带来了明显的优势,而非独立人士在爱尔兰更广泛的反移民运动中缺乏同样的认可或联系。
凯文·科伊尔在RDS Dublin RollingNews.ie的地方选举计票过程中
社交媒体的影响甚至可以在新政党的极右翼候选人身上看到,比如爱尔兰第一党的领导人德里克·布莱吉和爱尔兰人民党的罗斯·拉海。
布莱吉在弗莫伊获得5.5%的第一优先选择,一度看起来他将赢得地方政府席位,而拉海在科克市获得6%的第一优先选择,同样威胁要获得议会席位,但在周日落败之前。
和成功的独立人士一样,两人都参加了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因此在社交媒体上积累了大量粉丝,以至于他们与政党的关系已经成为候选资格的次要方面。
Derek Blighe(右)和Ross Lahive(左)在Cork Alamy Stock Photo的尼莫游骑兵计数中心
鉴于在社交媒体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极右翼人物取得了成功,讽刺的是,该运动对个性的依赖也阻碍了它的发展。
上周末极右翼候选人压倒性失败的一个因素是糟糕的选举策略,导致选票在各党派和独立人士之间分裂。
在都柏林市议会的巴利蒙-芬格拉斯区,超过20%的第一优先投票被四名极右翼候选人瓜分,但佩珀是唯一当选的候选人。
在芬格尔的布兰查兹敦-穆赫达特,另外三个人的支持率达到了16%,而国家党的帕特里克·昆兰同样是唯一一个超过这条线的人。
如果在许多地区有更少的极右翼候选人相互竞争,他们的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倍。
该运动的成员已经承认了这一现实,他们可能会考虑在未来9个月内举行的大选中采取更具战术性的方式。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爱尔兰第一的菲利普·德怀尔(Philip Dwyer)周一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段视频中说。德怀尔在塔拉赫特中央站了一站,但没有成功。
“唯一的遗憾是这次民族主义分裂的投票,我们都必须认识到下一次选举,这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Philip Dwyer(中)在都柏林市中心的抗议活动中
不同的极右翼政党和各种独立人士能否将其付诸实践是另一回事:人们不得不问,谁将领导他们,他们将如何制定自己的选举策略?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立了五个政党——其中三个是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成立的——这一事实表明,这个运动正在分裂,而不是团结起来。
他们的行为似乎并不表明凝聚力会很快下降。
今年1月,Blighe在X上发帖称,爱尔兰优先党不会在欧洲选举中提名候选人,而是支持其在爱尔兰自由党(Irish Freedom Party)的“合作伙伴”。
最后,布莱作为爱尔兰南部的候选人与爱尔兰自由党的迈克尔·莱希竞争,而菲利普·德怀尔在都柏林与戴曼德·奥康纳竞争。
与此同时,爱尔兰人民党承诺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在其品牌下竞选,而民族党则卷入了一场正在进行的领导权之争,导致詹姆斯·雷诺兹和贾斯汀·巴雷特——他们都声称自己是该党的合法领导人——在中部地区西北部的欧洲选举中相互竞争。
也许这样的党派之争是建立在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在社交媒体上,个性——而不是思想——是主要的吸引力: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明星,但没有人准备好扮演配角。
从这个角度来看,赫尔曼·凯利(Hermann Kelly)与斯蒂森和佩珀在大选后拍摄的照片似乎更加深思熟虑;在极右翼摆脱自我问题之前,这可能是他离荣誉最近的一次。
广告和支持公司的组合
贡献有助于使付费墙远离像本文这样有价值的信息。
超过5000名像你一样的读者已经站出来支持我们了按月付款或一次性捐款。了解更多支持杂志